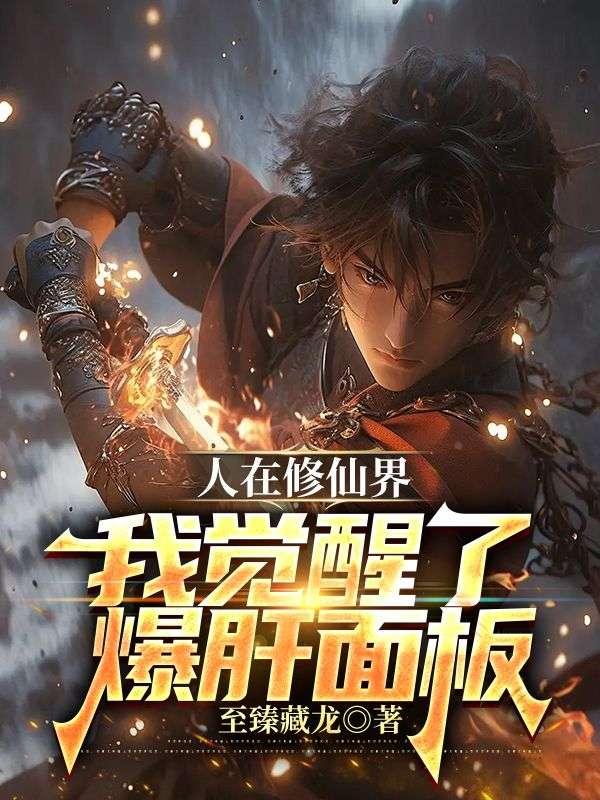落伍文学>我是限制文的女配 > 第37章(第1页)
第37章(第1页)
林听见段翎不想说到底是什么病,也没再问下去。毕竟他们不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关系,有点到即止的礼貌关心就行了。
“希望段大人早日康复。”她斟酌须臾,仍然将手中的帕子递了过去,“你还是擦擦血吧。”
流这么多血,当真不会晕?锦衣卫的身体都这么好的?
段翎对腕间流出来的血没多大感觉,习以为常,刚刚才没留意,也就没擦去。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眼林听递来的帕子,目光一顿。
鲜橙色的帕子上绣着几条歪歪扭扭的青色虫子。
林听顺着他视线看去,意识到拿出来的帕子恰好是她绣的。
林听跟他一起坐在树边,心里有些焦灼,她总觉得段翎的伤口在流血,偏偏他今天穿的黑色衣服,她偷偷看了好几眼,都看不出半点异样来。
再悄悄看一眼段翎的脸,一束从树隙中照下来的日光落在他的高挺的鼻梁和淡红嘴唇上。
好看,但林听没功夫欣赏。
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,她感觉段翎好像又白了点,不会是流血流的吧。
“你看够了吗?”
段翎忽然扭头对上她的眼睛,林听偷瞄的目光被抓了个正着。
她蜷了蜷脚趾,有点尴尬的把脑袋转正,然后默默道:“……看够了。”
段翎没再理她。林听已经好几年没这样生过病了。
她一直觉得自己壮的像头牛,以前总风里来雨里去的半点问题也没有。
乍来京城,就算不太适应这里饮食和天气,身体也没出现什么水土不服的反应。她还得意过一段时日。
结果现在如今好像都赶一起了。
皦玉给她抓了药,急急慌慌的熬给她喝,这会她脸蛋是真红成大番茄了,窝在塌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
一下午昏昏沉沉的闭着眼睛,在半梦半醒间还做了一个遥远未知的梦。
兴许是初秋时节,丛林树叶零落。
入眼是成片的青绿,狭窄小径泥土湿润,所有东西都被一层似有若无的薄雾遮挡着,她在一个很低很低的视角,想要看清大人的脸,需要很努力的仰起头。
她独自坐在长满青苔的台阶之上,一个接着一个高大又陌生的人从她身侧穿行。
虽没人理她,但她仍觉得自己是雀跃的,因为这里很久未曾这样热闹过了。
可她每日能出来的时间有限,只能在外面待小会儿。印象里在这里的每一天,她都过着宁静又毫无波澜的生活。
被困在方寸之地。
没人告诉她外面有什么。
直到一个傍晚,落日恢宏璀璨。
那只手轻轻牵住她,声音温柔:“我们去看落日好不好?”
她仰头想去看清他的脸,但那咫尺之距间,好像总隔着层经年不散的浓雾。
“师父说外面很危险。”
“没关系,我保护你。”
林听握紧了他的手,她依然执着的想去看见他,但越努力,梦境就越残破。
她紧紧抓着他的手,始终不愿意放开,结果在一切颠倒混乱之际,指节还是生生脱力,无论怎么抓紧都无济于事。
“姑娘?”
“姑娘你怎么了?”
遥远的声音突然砸进幻境。
皦玉无措的站在塌上,紧紧握住了林听抓着被褥的手,林听睁开眼睛,昏暗的烛光落进眼眸,窗外是沉静的天空。
金黄的晚霞遍布天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