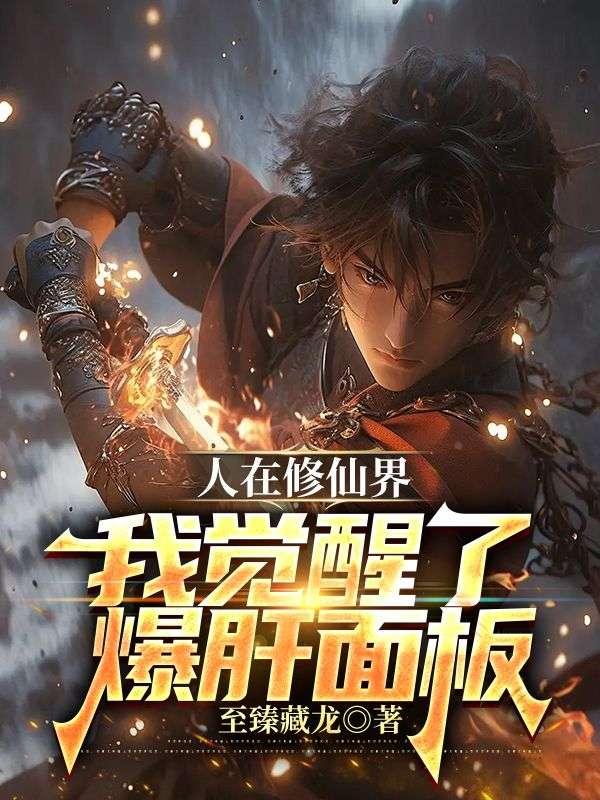落伍文学>禁止拐跑游戏[无限] > 第22章(第5页)
第22章(第5页)
入目的第一句话就令池殊瞳孔微缩。
【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逐渐清晰地、难以逃避地意识到一个真相,哪怕那多么残酷,就如同这该死的世界,令我深深地无力与痛苦——
我是个男性。】
他连忙往下看去。
【自出生起,我的衣柜里便永远堆满了裙子,巨大的镜子前全是精致的首饰。
她亲手打理我的头发,为它装点上美丽的花,不让任何女佣经手它。
她热衷于买入一切她看中的衣物——即使在家中最窘迫的时候——然后把自己关进房间里,一件又一件地试穿它们。
也许是那逐渐被岁月侵蚀的容颜与变形的身材打击了她,常常地,我能听见里面传来摔东西的声音,伴着歇斯底里的哭泣。
那些她不穿的衣物自然全给了我。她剥光我的衣服,亲手为我穿上它们,然后将我放在镜子前,温柔地抚摸我的脸蛋,赞叹着我的美丽,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人,而是一只廉价的洋娃娃。
每当我想拒绝,她就会疯了般地打我,将房间里能看到的任何东西砸到我的身上,又在之后伏在我的脚边痛哭流涕地忏悔。
几日之后,她又会忘了所承诺的一切,继续在我的身体上添加伤口。
她那毛骨悚然的执念令我害怕,日复一日,我终于学会了如何伪装一只被剥离情感的人偶,双眼空洞地任由她摆弄,露出她所喜爱的,“淑女的笑容”。
这时她会那些腻烦乏味的词句,一遍又一遍地夸赞我的美貌,如果我的表现好,晚上就有了上桌吃饭的权力。
没有为什么,这一切只是因为她想要一个女儿。
而在我出生后,她永远丧失了生育的能力。】
【我的家族,兰朗家族,曾是王室中最为辉煌的一支贵族。
但盛极而衰的命运却在数年前咬住了我们的尾巴,它们像蛀虫一样爬上来,吃空了里面的果实,连那一丁点难啃的核也不放过,最后不留体面地撕开了最外面的那层遮羞布。】
【兰朗家族的人都有疯病。
我的父亲在我出生前大笑着在火海中自焚而亡,我从未见过他一面,自外族嫁来的母亲也变得疯疯癫癫,我的哥哥阴晴不定,举止喜怒无常,他可以上一秒温柔地摸我的头发,下一秒把我的头狠狠往墙上撞。
那么我呢?我呢?我也是个疯子吗?
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
我不知道。
但即使没有,我想,也离它不远了。】
【它说他叫派克,派克,神明的侍者,侍奉至高无上的██,那位只在最古老的禁书里,以零星的字句提到的神。
它那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我,我看到自它的身后伸出无数黑色的触手,每一根仿佛都有着独立的生命,它们用我无法听懂的尖锐的声音交谈。但我一点也不害怕。
派克以绝望为食,人类的痛苦是最美味的佐料。它说很乐于“拯救”像我一样的人。
我问它是否所有人生来注定不幸,它发出古怪的、沉闷的笑声,仿佛声带的另一头连接着深海。
“并非如此。‘小姐’。”
“命运注定不公,而伟大的██会平等地向每一位行于绝望迷域间的人类投以注视,只要你承受得起的代价。祂会帮助你。”】
【我的哥哥,我亲爱的哥哥,佩利·兰朗,他让我半夜前去他的房间。
我或许能猜到他想对我做什么。
从他每当看向我时几欲穿透我皮肤的炽热视线,从他抚摸过我头发时突然加重的力道,从他那突然伸进我衣裙里滚烫的指尖,从他偷走我的衣物疯狂嗅闻时双眼猩红的模样……
那天晚上,我所剩无几的情感再一次从体内剥离。
我的灵魂木然地游荡在这座空荡的城堡,里面贵重的家具很多都已经变卖,许久无人清扫,爬满了老鼠与虱子。
就像我的生命。】
【当二十二点的钟声响起后,前往无人的院落,用荆棘刺破中指,他们的血液会引来恶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