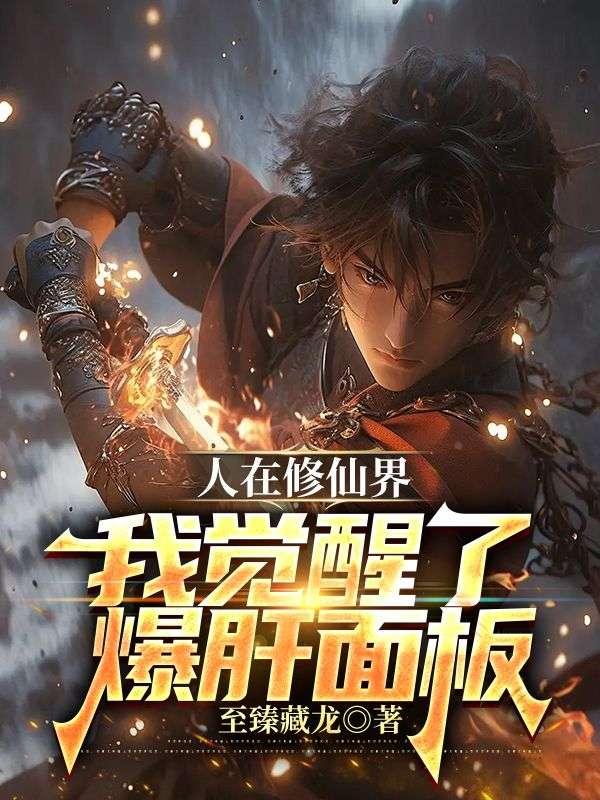落伍文学>凶悍屠户太旺夫[种田] > 第75章 筹谋(第1页)
第75章 筹谋(第1页)
柳金儿定了定心神,才鼓足勇气道:“你成亲的时候,我爹在交杯酒里下了毒。我本来想找许娇娘把酒要过去的,没想到阴差阳错,叫我娘先拿走了,她应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,后头又给了三婶儿。”
虽然早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,听到柳金儿一五一十说出来,柳天骄还是恨得咬紧了牙,“他怎么能那么狠毒?这可是杀人啊!”
“亲女儿都卖的,能不狠毒吗?那日酒壶叫三婶摔坏后,我爹怕三婶儿日后想起来算账,偷偷将酒壶碎片都捡起来扔进了湖里。但他不知道,我在他之前先捡了两块儿藏起来,就埋在老宅后面的香椿树下,你哪天有空,去悄悄挖出来吧。虽然不知道还能不能查出些什么来,总归也算是一个把柄。”
早知道自己家人是什么性子,柳金儿下意识里都在防备,见到他们偷偷摸摸凑在一块儿就忍不住上前听墙角。别说,这个小习惯还真帮她知道了不少事。
末了柳金儿又说,“还有一个事情,我不敢确定真假,只是听我爹和幺叔谈起过。”
柳天骄看她吞吞吐吐的样子就着急,“有什么直接说,真假不要紧,我自有法子判别。”
柳金儿避开了柳天骄的目光,小心开口道:“听说大伯被长虫伤得那么厉害是因为刚打死了一头熊瞎子,正是乏力的时候。”
难怪,他爹的身手可是能赤手空拳打死一头熊的,怎么会被长虫伤成那样。他爹又不是鲁莽的人,若有猎杀长虫的想法,必是先布好陷阱想好退路,然后一箭把长虫射伤,再上前搏斗。就算有失手,也不至于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
听柳金儿这么一说,柳天骄明白了,他爹运气太差了,才猎杀了一头熊就碰上了长虫,毫无防备又力竭的情况下,再厉害的身手也是枉然。
“那熊呢?”
“应当是被幺叔拿去了,我爹也知道此事。”
原来如此,他爹才去世的时候,柳老二闹得那么凶,就差没直接说他家的房地都是他二房的,柳老三柳老四都有意见,怎么偏偏柳老幺稳得住。现在看来他和柳老二是早就商量好的,柳老幺得了熊,柳老二就得田地。没想到两人算盘打得好,结果现在卖熊的钱柳老幺得了,田地还没影子,柳老二心里能舒服?
柳天骄努力压制住心中的愤怒,真心实意地跟柳金儿道谢:“多亏了你,不然我还真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。。”
“不用谢,除了你,也没人会关心我一句了。”柳金儿说得悲凉,心中却无比坚定。既然父母兄弟都靠不住,就不用了再顾及什么了,以后路都靠自己走,好也罢歹也罢,总归都是自己的,不再叫人摆布。
柳天骄阴沉着脸回了家,进了正屋就一把将卫文康手里的书扣在桌子上,然后把人抱进怀里,低沉着声音道:“心情不好,快安慰一下我。”
这是在撒娇吗?卫文康有些不确定地拍了拍柳天骄的肩膀,问道:“怎么了,谁给你气受了?”
柳天骄气得咬牙,“还不是柳家老宅那群畜生,拿了我爹的卖命钱,还想毒死你。”
卫文康蹙眉,“柳金儿跟你说的?”
“嗯,她说我爹被长虫害死之前曾猎杀了一头熊,那熊被柳老幺拿去卖钱了。还有咱们成亲那日的交杯酒,毒就是柳老二下的。”
卫文康也被柳家老宅的人恶心到了,“不择手段,不配为人。”
柳天骄嗡着声音道:“多骂几句,我爱听。”
这可有点难为卫文康了,村里骂人的话多得很,可他一心读书,又觉得骂人有失君子风范,实在是没有学上几句。但他家骄哥儿正伤心呢,可不能叫人失望。卫文康绞尽脑汁想出来一句:“相鼠有齿,人而无止!人而无止,不死何俟。”
柳天骄不满意,“说的什么鬼,听不懂。”
卫文康:“……要不我给你解释一下?”
柳天骄勉为其难,“好,给你个解释的机会,要是骂得不够脏,你改天给我蹲村口好好学习学习去。”
卫文康:“意思是老鼠尚有牙齿,人却不知廉耻,荏弱不知廉耻,还不如赶快去死。”
柳天骄咂摸了一下,“也不能说不好,就是太绕了,你直接说不知廉耻的人赶快去死不就得了。”
卫文康觉得不太对,“这是一种对偶的修辞手法,以鼠衬托人,你这么一改,意境全无,骂人的气势不就弱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