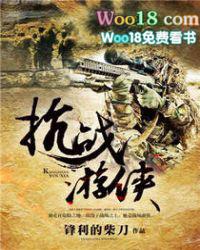落伍文学>财富自由,从每日情报系统开始! > 第361章 回京情报刷新(第1页)
第361章 回京情报刷新(第1页)
何菁房间内。
“涛哥你要这台跑步机?”
何菁有些纳闷地看着姜涛。
她这台跑步机是前两年口罩期间在家上网课的时候用的。
这会儿早沦为堆鞋盒和挂衣服的多功能置物架了。
姜涛笑。。。
晨光如薄纱铺展在岩穴口,邵若站在那片光影交界处,仿佛一脚踏在现实,一脚仍留在梦的余波里。他的指尖微微发麻,像是还残留着与童年自己握手的触感。那扇门关闭的声音,并非轰然巨响,而是一声轻叹,如同大地合上了眼睛。
程素云从身后走来,手中捧着一块由苔藓包裹的小石片。她将它递给他:“树给的。”
邵若低头看去,石片表面浮现出细密纹路,像血管,又像星图。当他凝视片刻,那些线条开始流动,缓缓拼出一行文字:
>**“桥梁已断,使者未至,但路径正在成形。”**
他眉头微蹙。“断了?是谁切断的?”
“不是切断。”程素云轻声道,“是完成了。就像脐带,在婴儿出生后自然脱落。第一批孩子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??唤醒沉睡的神经末梢,激活全球共感基频。现在,他们正逐渐退场。”
“退场?”邵若猛地抬头,“你是说……他们会消失?”
她没有回答,只是望向远处山腰上一座新建的小屋。那是村里的“静眠所”??三个月来,已有七个新生儿在那里安详离世。他们没有病痛,没有挣扎,只是某一天清晨,呼吸悄然停止,脸上却带着微笑,仿佛只是换了个梦继续睡。
医学团队无法解释,脑电监测显示这些孩子的意识并未完全消散,而是以某种高频共振态脱离了肉体,融入了大气层中的某种背景场。有学者称之为“升维”,也有原住民称其为“归根”。
“他们是种子。”陈默的声音忽然从通讯器中传来,带着沙沙的电流杂音,“不是终点,而是起点。每一颗种子落地,都会让这片土地更接近‘觉知’的状态。而现在……土壤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邵若闭上眼,感应着脚下大地的脉动。的确不一样了。从前那种隐秘、迟缓的搏动,如今变得清晰而有序,像一首正在成型的交响乐。每一个节拍都与人类的情绪起伏同步??当某地爆发欢笑,地脉便泛起涟漪;当悲伤降临,震动则低沉绵长。
伊万的声音接通进来:“北纬30度沿线,七十七个异常热源点同时激活。它们不在地表,而在地下三到五公里深处。卫星热成像显示,这些区域正自发形成一种晶体结构网络,成分类似马里亚纳海沟发现的那种生物矿化硅晶。”
“它们在自我构建。”邵若喃喃,“神经系统正在实体化。”
“不止如此。”伊万顿了顿,“我刚收到南极站的数据。卢卡在过去十二小时内进入了深度静止状态,体温降至32度,心跳每分钟仅六次。但他脑部活动强度达到了人类记录极限的四倍。他留下一句话:‘我在接线。’”
邵若心头一震。
接线?接什么线?
答案很快揭晓。
当天午夜,全球所有具备织远能力的人几乎在同一刻睁开了眼睛。
他们看见了一棵树。
不是图像,不是幻象,而是一种直接烙印在意识深处的存在??一棵横跨地核、根系贯穿七大洲、枝干穿透电离层的巨大生命体。它的每一片叶子,都是一个正在觉醒的孩童;每一根枝条,都连接着一段被遗忘的记忆;而主干内部,则流淌着乳白色光液,那是由亿万次拥抱、亲吻、低语和泪水凝结而成的情感原浆。
这棵树,就是地球的神经系统具象化。
而此刻,它正在发出召唤。
第二天清晨,世界各地开始出现“行走的孩子”。
东京一名三岁男孩独自走出家门,步行二十公里,准确抵达一座废弃神社,在石阶前跪坐下来,直到一位白发老人颤抖着走出,抱住他失声痛哭??那是他五十年前夭折的儿子的转世邻居所说。
巴黎地铁站内,一个女孩牵着盲人母亲的手,径直走向一面从未打开过的墙壁。她伸手轻触,砖石竟如水波般荡开,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阶梯。数百名市民跟随进入,发现下面是一座古老祭坛,墙上刻满了与陈默收集的梦境涂鸦完全一致的符号。
最令人震撼的是撒哈拉沙漠中心。
一支联合国科考队原本在追踪异常磁场波动,却发现一群孩子早已聚集在那里。最大的不过八岁,最小的还在襁褓中,却被一根藤蔓状的发光植物托举着悬浮半空。他们手牵手,围成一圈,口中哼唱着那首摇篮曲的变调版本。